发布日期:2024-12-17 11:16:33 浏览次数:186
也许大家可以一眼认出下图左边的玉米 (Zea mays),但玉米旁边是什么植物的种子?是小麦 (Triticum aestivum)的?也可能是水稻 (Oryza sativa)的?或许可能都不是。

图1 玉米和大刍草籽粒 (J. Doebley, 2004)
这个具有坚硬外壳的种子恰恰属于玉米的祖先——大刍草。如今的观点认为,小颖大刍草亚种 (Zea mays ssp. parviglumis)和墨西哥高原大刍草亚种(Zea mays ssp. mexicana)为现代玉米的祖先。
当第一位史前智人将随手拣来的植物作为食物之时,人类的发展就注定与植物无法分离。而作物育种也冥冥之中随着人类进步不断更新换代,历久弥新。作物也从无人问津的杂草逐渐变为了司空见惯的作物,这其中的改变蕴含着人类最原始对美的追求。育种,是一门科技与艺术交融,优雅的学科。
何为育种
WiKipedia中将作物育种定义为了“一门改变植物性状来获得理想特征的科学”。《园艺育种学》中将育种定义为了“针对育种目标,选择适当的种质资源,采用合理的育种途径,育成新品种的过程。”在我看来,育种的过程是人为施加选择压的一种“非自然选择”,通过改变作物原有的演化方向及速度,在短时间内获得稳定遗传、满足理想目标的作物品种。对于杂种优势育种来说,则亲本是稳定遗传的。
何为艺术
育种的历史
人类作物育种的历史不仅见证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也是科技发展的缩影。目前主流的观点将人类的育种史分为四个阶段 (Wallace, Rodgers-Melnick, & Buckler, 2018):
育种1.0时代:驯化(10万年前)
由于“新仙女木事件”,远古智人不得不捡拾起不起眼的草籽充饥,这也开启了人类与作物爱恨情仇的育种(驯化)时代。在这个阶段,人们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性地种植和收获,逐渐驯化野生植物,形成了最初的栽培作物。这段时间里,人类多数选择了充饥的食物,也慢慢演化成我们如今所习惯的主粮作物。其中,最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人类居然将文章开头提到的大刍草这种外壳坚硬、不可直接食用的杂草通过人工选择不断驯化成了今天软糯香甜的玉米。私以为,驯化就是生物演化最快速的体现,通过长时间的基因变异以及人工筛选,培育出更适合人类的品种,但驯化的弊端也充分显现——驯化时间过长。据考古证据表明,一类作物的驯化往往需要千年乃至万年的时间,这放在自然历史上无疑是一次伟大的壮举,但是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时间就是一切,同时,由于缺乏遗传理论的助力,依靠朴素的筛选观念注定不是人类育种最终的选择。

图2 作物及其祖先性状 (J. F. Doebley, Gaut, & Smith, 2006)
育种2.0时代:杂交育种(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
20世纪初,随着奥地利的神父在教堂后花园中,以一己之力打开了现代遗传学的大门,科学家开始探索遗传和变异的奥秘。这一时期的标志性技术是杂交育种。通过不同品种间的杂交,集中优良性状于一个个体,培育出新的品种。最值得注意的要数袁隆平老师团队所研制的杂交水稻,通过不育系、恢复系和保持系搭配,育成了雄性不育水稻,实现了水稻育种的“大跃进”。目前该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两系法,国内外的科研人员也在探索着一系法的可能性。放眼于育种产业,短期内杂交育种仍然是中国乃至世界育种的主流方法,但是其效率低的缺点也日益明显,新品种培育一般需要10年以上,而且很难选出突破性品种,一粒优质的种子的背后往往凝缩着育种工作者数十年的心血。

育种3.0时代:分子育种(20世纪末)
实际上,在选择育种时代里,研究者已经将作物性状和基因联系到了一起,其中最耀眼的发现就是诺贝尔奖得主McClintock在玉米上发现的基因转座现象,在DNA结构未被完全破解的前提下,这无疑是个跨时代的发现(Feschotte, 2023)。基因转座现象,简单地说就是在基因水平上进行的类似“Ctrl C + V”的行为,基因上的某一段基因,我们通常称之为转座子(Transposons),可以将自身复制到基因组的其他地方。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基因的物理意义没有明确,人们利用基因进行育种可以说是盲人摸象了。当1953年,DNA结构被完全解开,生物的世纪也悄然而至,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也让育种的研究享受到了时代红利,揭开了基因控制生物性状的秘密(Antoshechkin, Bass, Il'ina, & Frank-Kamenetskii, 1966)。同时,转基因技术也开始广泛应用于育种领域,使得育种变得更加高效。科学家能够通过转基因技术和基因编辑等手段,快速改良作物性状,培育出满足特定需求的新品种。生物的基因是由ATCG四种碱基通过排列组合形成。基因则是生物的遗传信息,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生物的性状(如玉米的株型、番茄果实的大小等)。作物基因编辑则是通过改变碱基的排列,从而影响植物的性状,使其获得较高的经济价值。分子育种允许育种者根据特定的育种目标来选择具有理想遗传组成的品种。这种方法可以用来改良作物的产量、品质、抗病性等重要性状。对于植物乃至生物来说,有时改变一个碱基可能植物的性状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因此,基因的精准编辑是无数育种科学家梦寐以求的追求,这期间诞生了许多诸如ZFENs、TALEN等基因编辑技术 (Bedell et al., 2012; Gupta et al., 2012),但因其脱靶率高、编辑效果差、编辑步骤繁琐等缺点,没有在育种领域大力推广,更多的还是以“粗糙”的分子标记技术辅助的育种。上天似乎有意无意地安排了这次历史进步,CRIPSR-Cas9基因编辑技术横空出世 (Shan et al., 2013),大大提高了基因编辑的准确性和精确性,该技术也毫无疑问地迅速取代之前的技术,实现了一次飞跃性的育种革命。我国的高彩霞老师就是世界作物编辑育种的领军人物,前沿的研究使得我国在育种领域走得超前,走得踏实。
育种4.0时代:设计育种
这一阶段,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对于特定性状的定点改造,科学家们开始着眼于作物系统育种,他们基于基因模块及其非线性耦合理论,借助计算生物学和人工智能的工具,设计出理想的品种。这不仅大大缩短了育种周期,也提高了育种效率。我认为其中最有趣的就是李家洋老师在2021年与多方合作提出了从头驯化野生异源四倍体水稻策略。他们将该策略分为四步:第一步,选择从头驯化合适的亲本材料;第二步,搭建包括参考基因组、基因功能注释、转基因及基因编辑系统在内的技术体系;第三步,设计和快速基因组编辑,通过多基因组编辑引入驯化相关基因或等位基因;第四步,新品种推广,包括对经过基因编辑的水稻品种进行区试、品试,以及新作物的认证和普及推广 (Yu et al., 2021)。这种“大道至简”式的育种方法无疑是对设计育种最好的阐释。

图4 从头驯化异源四倍体水稻路线图 (Yu et al., 2021)
据统计,全世界目前有超过1750个基因库,包含70万份种质种质,包括栽培品种、地方品种和野生近缘种,这些资源的潜力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开发。在如此庞大的资源中,人工挖掘就如大海捞针,低效且高代价。与传统方法相比,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这个以大数据分析和模式识别方面的实力而闻名的技术,可以从高通量组学数据、种质数据中提取更有用、更精确的特征,目前彻底改变了作物育种。当下,AI已被有效地用于预测母代和亲本玉米植株的基因组杂交,从而有助于识别突变率较高的基因组区域 (Farooq et al., 2024)。此外,基于玉米植株在胁迫下生长的DNA甲基化模式,研究人员使用人工智能方法来识别和表征基因组区域,从而区分功能基因和假基因 (Farooq et al., 2024)。AI的助力不仅在于对于已有数据的挖掘整理,更在于它可以自我学习,具有创造潜力。近日,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的汪海老师团队就利用17个植物物种的60万个基因以及6256套转录组数据,开发出了PhytoExpr的模型,对于改进作物自然启动子及从头设计新的调控因子提供了无限可能性 (Li et al., 2024)。个人认为,2024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从头设计蛋白技术 (De novo protein design),未来在新型设计育种中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Kortemme, 2024)。

图5 PhytoExpr模型架构(Li et al., 2024)
育种的艺术
基础研究的集大成
相信不少植物领域的研究者们无论是在撰写论文还是申请基金写本子的时候,研究意义的最后总会加上一句“为培育新品种提供优质的候选基因”诸如此类的话。这无疑是育种的价值所在。笔者认为,当下的科学研究可以分两类,一类是兴趣导向的自由探索式研究;另一类则是需求导向的提本增效式研究。目前大多数研究可能归类于后者,植物领域也不例外,这也恰恰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植物乃至自然的认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包括白菜等十字花科植物、土豆等茄科作物在内的许多植物具有明显的远缘杂交障碍的现象,使得其杂交育种很难进行,上个世纪,研究人员巧妙地利用了花粉蒙导效应 (Pollen Mentor Effect),解决了远缘杂交育种难的问题。前辈在实践中所发现的现象背后的秘密,直到2023年才被瞿礼嘉老师团队揭开 (Lan et al., 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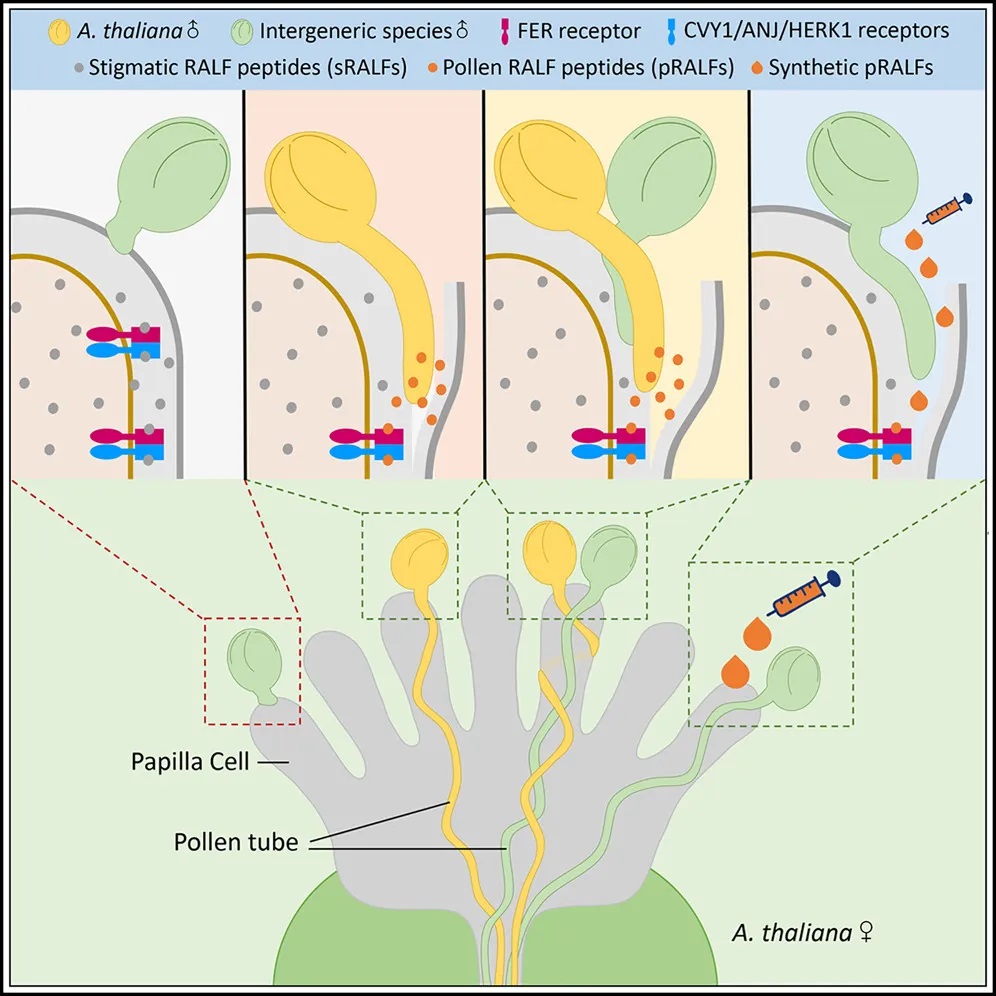
图6 被子植物花粉蒙导效应的分子机制 (Lan et al., 2023)
同时,育种还推动了人们自然追溯历史的好奇心,促进了物种演化的研究。番茄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蔬菜作物之一,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它不仅是重要的食品来源,也是植物和肉质果实生物学研究的模型系统。黄三文老师团队分析了360份不同品种的番茄基因组。通过重测序,产生了大量序列数据,识别出超过1100万个单核苷酸多态性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SNPs)和130万个小的插入/缺失(Insertion-Deletions,InDels),揭示了番茄育种历史上的两个独立阶段:驯化和改良。驯化阶段主要集中在提高果实大小,而改良阶段则进一步增大了果实并引入了其他农艺性状 (Lin et al., 2014)。此外,育种的需求还变相推动了生态学、园艺学、土壤学、病理学等各个学科分支的发展,可以说育种是一门蕴含科学之美的综合科学。

图7 番茄的演化路径 (Lin et al., 2014)
实践中的艺术性
如果把原始材料比作画纸的话,育种家们则是站在画纸前的画家,基因则是他们的调色盘,最后的成果(也就是品种)全靠育种家把握。育种家们似乎对自然敏感的人,对于气候、土地有着异于常人的判断力。制定育种目标时,他们充满想象力,田间育种时,他们是挥斥方遒的将军。在育种过程中,很多优质目标可能是互斥的,如果想要酸甜可口的番茄,就必须要牺牲其决定耐贮性的硬度。育种家对于品种性状分配的把握,往往最后决定了该品种的推广度,而这种把握,可能有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感。笔者在育种课的时候有一种深刻的感受,这些身处育种一线的老师多少是带点理想主义在身上的,他们会痛斥那些分离品种而育成“新”品种的现象,也会回忆起自己挥汗田间的光辉岁月,他们可是手握多个优质品种的大牛老师啊。更有夸张的说法,光是去欣赏和品尝某个品种的作物,经验老道的专家可能就能立马分辨该品种出自哪位育种家之手。可能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品尝的是优质的蔬菜,但对于行内的育种家来说,他们则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可以说,育种是尽显实践中科学艺术的平台。
人与自然的博弈
植物在经历亿万年的自然演化后,已经形成了复杂的基因以及与环境互作的分子网络。曾经有学者将目前最精密的计算机和人脑做比较,发现人脑比世界上所有计算机都更加复杂更加精确,私以为植物演化也有如此精密的排布。植物作为一个生物系统,在选育性状的过程中,需要谨慎乃至细致的“排兵布阵”马铃薯作为重要的粮食作物,传统栽培的马铃薯是同源四倍体,基因组复杂,育种进程缓慢,且主要通过薯块繁殖,存在繁殖系数低、储运成本高、易携带病虫害等问题。原有绝大部分的二倍体马铃薯自花授粉后不能产生成熟的种子,同时,传统育种过程中积累的有害基因突变,会造成马铃薯繁殖力和产量下降,即自交衰退。黄三文老师团队就此提出“优薯计划”,旨在用二倍体马铃薯替代四倍体、用基因组学和合成生物学指导马铃薯育种在探索的过程中,他们已经成功培育出了第一代高纯合度(>99%)的二倍体马铃薯自交系和杂交马铃薯品系“优薯1号”。试验显示“优薯1号”的产量接近3吨/亩,具有显著的产量杂种优势,同时还具有高干物质含量和高类胡萝卜素含量的特点,蒸煮品质佳(Zhang et al., 2021)。这无疑打破了二倍体马铃薯无法育种的“自然规律”。二倍体马铃薯育种也意味着可以摆脱原有的薯块育种,转而更加轻便的种子育种。种子在运输过程中,及其轻便且不易变质,此外,种子育种可以大幅度缩短马铃薯的育种周期,从原有的10~13年缩短到3~5年,或将引起一轮马铃薯的“绿色革命”。这其中尽显不甘平凡的人性之美。可以说,育种是人类与大自然的抗争,以弱小搏击巨浪的征途。

图8 马铃薯薯块与种子比较图 (图源网络)
总结
传统的农业“靠天吃饭”,人类在大自然的庇佑下生存繁衍,而如今随着以育种为目标的基础研究的壮大,传统农业的势态也逐渐过去,转而更加精密可控、更加有秩序的农业正在崛起。应对极端气候环境,育种技术能够培育出高产、耐旱、耐盐碱、抗病虫害的作物品种。这些品种能够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实现更高的产量,减少对化肥和农药的依赖,降低农业生产的环境负荷,从而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育种使得“将饭碗端在自己的手中”不再是空话,更是全人类一块一块砖垒起的高塔。
在这篇历经千万年的乐曲中,我们不仅见证了科技的力量,更感受到了人性的光辉。育种,这门古老而又年轻的艺术,将继续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流淌,不断演绎着生命的奇迹。在未来的篇章里,愿我们能以更加敬畏的心态,对待每一粒种子,每一片土地,共同守护这份来自大自然的宝贵馈赠。
后记
该文章的起因是“新生园艺专业介绍”的结课论文。
作为大四即将毕业的学生,我第一次走进“新生园艺专业介绍”的课堂,仿佛在短时间里浏览了四年本科生涯的学习画卷,从大一的数理化基础课,到大三的专业必修课,园艺专业一步一步地将我领入了生命科学的殿堂。私以为,在本科繁杂枯燥的课程中,唯有园艺作物育种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震撼。在这门课中,身处科研一线的老师们带我领略了老一辈育种家们踏实求真的理想主义,也带我初探了现代设计育种的魅力。在育种这门课中,我仿佛窥见了整个大农学育种乃至生命演化的辉煌画卷。
致谢
感谢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闫军老师对该文章的总体指导,闫老师一针见血的点评让我学习到了很多文章写作的技巧和方法。感谢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王向峰老师的帮助,给我推荐了闫兵老师。感谢四川农业大学的赵傲雪同学对该文章细节的修改。同时,感谢园艺作物育种学的授课老师们,他们分别是沈火林老师、孙亮老师、杨文才老师和程青老师,是你们让我领略到了育种的艺术。
参考文献
1. J. Doebley, The genetics of maize evolution. Annu Rev Genet 38, 37-59 (2004).
2. J. G. Wallace, E. Rodgers-Melnick, E. S. Buckler, On the Road to Breeding 4.0: Unraveling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Boring of Crop Quantitative Genomics. Annu Rev Genet 52, 421-444 (2018).
3. J. F. Doebley, B. S. Gaut, B. D. Smith, The molecular genetics of crop domestication. Cell 127, 1309-1321 (2006).
4. A. Sohail, C. Lu, P. Xu, Genetic and molecular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male sterility in rice. J Appl Genet, (2024).